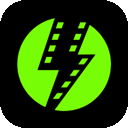醉后狂鞭名马,下一句引发无限遐想!
作者:佚名 来源:未知 时间:2025-02-02
曾经酒醉鞭名马,生怕情多累美人

“曾因酒醉鞭名马,生怕情多累美人”是郁达夫的两句诗,原诗全文如下:
“不是尊前爱惜身,佯狂难免假成真。
曾因酒醉鞭名马,生怕情多累美人。
劫数东南天作孽,鸡鸣风雨海扬尘。
悲歌痛哭终何补,义士纷纷说帝秦。”
此诗写于1931年早春,郁达夫年35岁。从1921年10月至1931年1月,郁达夫用十年的心血完成了自传体小说《沉沦》《迷羊》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和自传《郁达夫自传》,这四部小说都是以作者自身为模特儿而写成的自叙传。而此时的郁达夫正处于情感低潮期,其爱妻孙荃正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,在富阳老家;情人王映霞已和他劳燕分飞,并发表《一封公开的情书》,声讨郁达夫;工作也颇不顺利,于1930年辞去了安徽省教育厅长的职务,到了上海和杭州,任中华书局编辑和浙江省政府参议。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,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,他自感失意彷徨,所以诗中“生怕情多累美人”中的“美人”并非实指某一人,而是对当时处境的一种概括和形容。
关于“曾因酒醉鞭名马”,有两个版本的故事。一个版本是郁达夫年轻时在东京的某次酒醉后,将他的好友、著名的报人兼作家邵洵美的坐骑误认为是自己的马,而挥鞭怒抽,引起了一场风波。事后,郁达夫向邵洵美道歉,两人一笑置之,并因此结为忘年好友。但此事缺乏佐证,在两人的回忆录中都未曾提及。
另一个版本则是关于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,应长兄郁曼陀之邀,参加当地名士举办的宴会,因对时局和名人名士们的矫揉造作感到不满,便发酒疯,用筷子刺破了一位名士的鼻孔,又将一位名士的假发套摘掉扔到火锅里,从而得罪了当地的一些权贵,被取消留学资格,遣送回国。这个版本,见于郁达夫在1923年写的自传体小说《沉沦》的序言里,文中写道:“从一九一九年七月到一九二二年的夏天,这一个时期当中,我的思想变动得很剧烈。普通的凡人,从早到晚,为生活而劳动,是不知有什么思想变化的。即使有之,也都是如微尘细粒伏藏在沙滩里,看不出什么痕迹来的。但我的思想,却偏要如春草般地从沙里透出来,虽然被石头压住了,还是要从石头缝里透出芽来。”又说:“我的日记,从前是每日必记的,但一到了日本,连记日记也懒得记了。并且我所带的几本旧日记,在到日本的第二年的春天,为了某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故,一气之下,几乎把它完全烧毁了。现在剩下来的,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,且都是和这一次所要说的话没有多大关系的断片。所以我对于这一次的日记,更觉得有保存的必要了。因为这一年的日记,总算把我的思想变迁的痕迹留下来了。在这一年之中,我共计变了三次主意:第一回是,我想学德文,将来去德国留学,读一点文学书,将来也能做几篇小说出来。第二回是,我劝我的朋友学农回去,我自己也想回国去研究植物学。第三回是,丢开了植物学,心理学,文学等等,一心一意只想学经济,将来想在中国做一篇改造农村的大文章。”文中的“某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故”,就是指他酒醉鞭名马,惹祸上身,被迫回国一事。
而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《沉沦》里的主人公“他”,其实就是作者自己,只不过是把事情挪到了中国的留学生身上。书中这样写道:“他”因“支那人”的侮辱,就于某一天晚上,一个人上酒馆去喝酒。他喝醉了,竟拿了酒店里一只筷子,走上街去,看到路上有一辆汽车里的马车夫,正在叱骂他的马,他无端地暴怒起来,跑近汽车,把筷子向那马车夫掷去,把马车夫的手臂掷出了一个血洞。又一回,他上野外的公园里去散步,一高兴竟在公园里的草地上睡了起来。醒来的时候,他觉得有一个人正在抚摩他的头,举头看时,却原来是一个年老的车夫。这时候,太阳已经下山了,远望市街上的电灯已上得通明。他觉得肚子饿了,就跑进那车站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去吃酒。那酒馆里人很多,他在角隅上坐下了,喝了两三杯闷酒,吃了几碗冷饭,又发起酒疯来了。他同酒馆里的人打了起来,又因为打了人,被警察抓住了,罚了他三十元的钱。钱是没有的,结果只得把身上的一件棉袍子脱下来做了抵押。他一边在路上乱走,一边在嘴里乱骂,不知骂了些什么。到了旅馆里,他已经累得一丝力气都没有了,但他还想到那个老车夫上来。他想:“他为什么对我那样地好?他绝对不是好人!他一定看上了我,想来骗我,所以假做好人来接近我的。”想到这里,他就怨恨中国人,更怨恨那个老车夫。他想:“中国人真是一个下等的民族!我是再也不能和他们混迹的了。最好是寻一个机会,和他们大家同归于尽。”
《沉沦》出版后,风行一时,尤其是受到了青年学生的喜爱,甚至被看作是青年们的“枕边书”,连茅盾都感叹说:“达夫是创造社中唯一的一个创造社时代的全盛时代的诗人。他在1921年4月出版的《沉沦》是那样的受青年读者所欢迎,恐怕在当时的青年中间,谁都读过他的《沉沦》。”郭沫若也赞誉他是“中国文坛的泰斗”。而郁达夫,也因此一举成名,从此开始了他“文名与爱情”双丰收的浪漫人生。
郁达夫的一生,都在追寻爱情。他曾说过:“曾因酒醉鞭名马,生怕情多累美人。”他还说过:“大抵男女之间,尤其是以学识思想为基础的,最能相敬如宾,白头偕老。”他也曾公开表示:“在男女两性间,爱的意义是比‘被爱’要神圣的。尤其是男人,我敢于说,男人若不能真正的爱过一个女人,他的灵魂,他的世界,他的人生,终将有若一部没有彩图的《圣经》。”但这位敢于宣称“没有恋爱的生活不是生活,没有爱情的人生,就不是人生”的才子,最终还是在爱情中迷惘,在婚姻中挣扎,直至生命的尽头。